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五日
老媽,
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慈善家;我和基督完全相反,而且慈善工作對我來說並沒有任何說服力。但 為了自己所抱持的信念,我倒是會不惜一戰,設法把將對手打敗,絕不讓他們把我釘到十字架上或者其他任何地方。至於那場絕食行動,你完全搞錯了。事實上,我 們發動了兩次:第一次絕食時,在我們二十四位囚犯中,當局就釋放了二十一位;第二次絕食時,當局宣布要釋放領導人菲德爾.卡斯楚,明天就要執行了。要是他 們真的說話算話,那麼在獄中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一個人。我不希望你會以為,我們兩人就像伊爾達所暗示一樣,是因為作為犧牲品而繼續被關在獄中。我們之所以無 法獲得其他同志的待遇,只不過是因為證件不全而已。我打算流亡到最近的國家,並且在當地尋求庇護,不過由於我在美洲大陸已出了名,所以不可能不遇到困難。 看看找到什麼地方可以待,我就在那兒養精蓄銳,待有需要時再貢獻一己之力。還是要再說一次,我很可能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無法寫信。
真正讓 我覺得受挫的,是你不理解我之所以這樣做的意義,還有你總是命令我要適可而止、多替自己想想等等――那是最低劣的個人品行。我不僅不會適可而止,而且永遠 不會試著適可而止。我內心神聖的火焰已變成了一盞微弱的小明燈,我至少有了一點點自知之明。你建議我多少要替自己想想,但這是一種麻木不仁和軟弱的個人主 義說詞;必須要讓你知道,我很努力地要消除我內心中殘存著的這些二十世紀品行。我不是指自己過去膽小而且沒有自知之明的時候;我是指那個過著波希米亞式流 浪生活、不關心鄰居、只管自掃門前雪的那個自己,當時這些想法是因為曾經意識到自己的生存能力(姑且不論這是否對自己估計錯誤)。在獄中的這些日子,加上 前陣子受訓的階段,我已經完全和戰友同志們產生了認同。我記得自己曾經有過一些愚蠢的(或起碼是奇怪的)念頭――我與戰友們產生了完全的認同感,結果 「我」這概念腦海中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「我們」。這是共產主義的原則,當然這聽起來好像是一種誇張的宣傳,但這種無我的團結境界,曾經讓我著迷,現在還 是一樣。
(信紙上不是血跡,只是番茄汁而已。)
你以為適可而止或者「多少替自己想想」是重大創舉和藝術創作的泉源,這真 是大錯特錯。任何偉大的作為都需要激情,而且更需要膽識,這是人類普遍擁有的特質。你還有一點讓我覺得奇怪,你屢次提到上帝老爸,我希望你不會變回年輕時 那樣地溫馴。我還要提醒你,那一批求救信並沒有什麼用:比特在自欺欺人,里茲卡(Lezica)不願意面對問題,他罔顧我的指示,竟然跟伊爾達講了一堆有 關政治放逐犯的責任。勞爾.林區(Raúl Lynch)人很好但不並熱心,巴帝亞.尼爾比奧(Padilla Nervio)表示這不是他們部門的事。他們都願意幫忙,但條件是要我背棄理想;我想你也不希望你的兒子苟且偷生,猶如巴拉巴一樣(Barabbas); 我想你會情願自己的兒子因為做了該做的事而殺身成仁。這些求救信只是徒然增加他們和我的壓力而已。
我再說一次,在古巴成功撥亂反正之後, 我要去那兒都行;但要是被關在某個機構或某家治療過敏症的診所中,那我肯定會完蛋。總而言之,這種傷痛,這種身為年邁母親並且希望自己兒子活下去的傷痛, 是可敬的,我不單必須珍視它,而且樂意珍視它。想見見你,不是為了安慰你,而是為了安慰偶爾會暗地裡思鄉的自己。
給你一個吻,老媽,要是 沒有什麼狀況,我一定會去看看你。
你的兒子 切
Tuesday, July 06, 2010
Subscribe to:
Post Comments (Atom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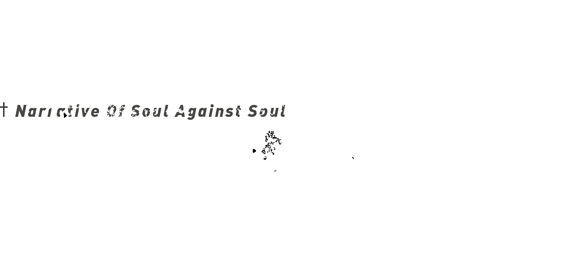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